再也不会长大
八十岁之后,我的外婆再也没过过生日。她总说,生日是个槛,人越老越不想过。
我二十岁之后,日子如白驹过隙,果真,我对自己的生日也没那么期待了。
今年立冬的凌晨,西安倏尔大雪,这是在江南从未见过的景象。他们说,一片大雪就是一股思念,那我的思念也冻了厚厚的一层吧。
很久以前在南方,外婆把日历撕下来,整齐的一叠。日历纸很薄,节假日红色,平时绿色。外婆的一天就是一张纸,日日分明。
年关将近,日历变红的时候,我就能见到外公外婆。那时我七八岁,记忆里总是在月明星稀的夜里走回家。月光下,野荡漆黑的水面泛起点点银光,芦苇婆娑。低头赶路,土路深深浅浅,远处家里一盏昏黄的灯渐渐清晰。屋外无限得冷,可心里却温暖——就要到家啦,那是独属于我的温暖。
进了院门,外公外婆就会迎出来,拴在门房的黑狗也要扑上来舔我的脸。我们一家在院子里用力地跺脚,抖掉一路的风尘,把那一年所有的辛苦和委屈也都留在门外。家里跛脚的老猫被惊醒,抬头“咪呜”一身,又蜷身睡去。
夜深了,关灯,我盖上厚厚的棉被,半梦半醒地听我妈和外婆说话。村上的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,说不清也说不完。隐隐听见远处的火车驶过。我躺在床上,像躺在一条古老的船上。
外公外婆的家永远不关门。他们的儿女,儿女的儿女,匆匆出现又消失,每年来这聚一下,然后再开枝散叶。我们渐渐长大,外公外婆也老了。
五年前,外公生了重病,吃不下饭,毫无办法。外婆孤单又无助。妈妈打电话给外婆,让她打米糊、熬中药甚至找偏方,外婆一一照办。外公的起居都靠她一人照料。可是外公还是一日日地病下去。终于有一天,妈妈又打电话嘱咐她,外婆忽然落泪:“我十六岁就嫁到这个家,年轻时照顾你爸的妈,老了又照顾你爸,一辈子……我去给你爸热粥了。”妈妈默然。
我忽然想起童年时的很多事情,想起了我瘦小的外婆。她从来没有这样脆弱,但她也从来没有缺失过对这个家的爱,她有自己的方式。
江湖夜雨十年灯。转眼我就二十一岁了,过了二十岁,我一直在想,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、活得不平凡。我在远远的西安想着这些,想起了许多猝不及防的相遇,想起了许多后知后觉的告别,想起了我的亲人,我的童年。
我渐渐认识到,一辈子只有一次,爱别人胜过爱自己——虽然就一次,也很不容易。
长大是一件辛苦的事情,但爱不是。我们都在长大,但我们都忘了给自己一个必须去爱的理由。
外婆家的院子里有棵硕大的柿子树,秋天到了就结满金黄的柿子。有天我在树下捡到一个小柿子,翠绿、坚硬,一股苦寒香,冒着青春期特有的幼稚和傻气。我把它送给外婆,外婆对我说,它再也不会长大啦。
它再也不会长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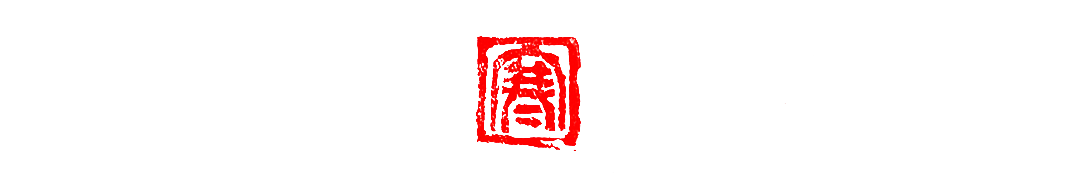
作于2021年11月9日


